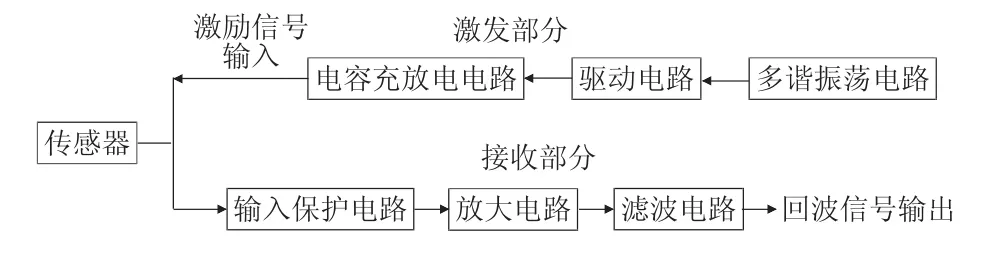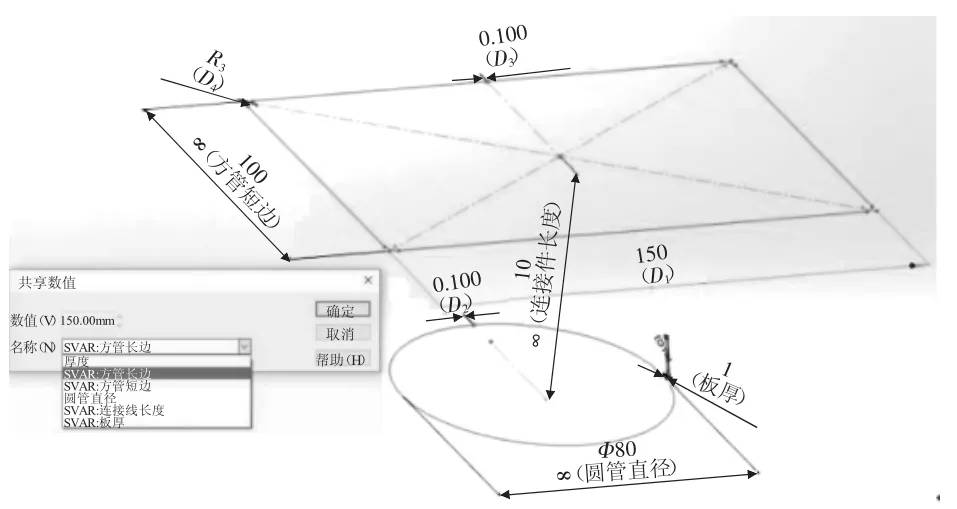王君芳,韩国栋*,王召明,云锦风,秦 洁
(1.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2.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草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占国土面积41.7%,是重要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载体,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部分地区草原生态明显恢复[1],但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脆弱,草原生态形势依然严峻[2-3],草原生态修复面临资金短缺与技术匮乏的双重挑战[4]。“十四五”期间,我国提出实施退化草原修复1.5×107hm2,采用自然与人工促进相结合方式恢复草原植被,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5-6]。随着草原生态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7],要从遵循顺应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增强草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针对性、长效性,促进草原自然恢复,提高草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工干预引导自然恢复理论,是解决草原生态修复的重要理论[8-9],可以应用在草原生态修复全过程。通过自然与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手段,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修复、重建和改进,并持续、稳定、健康运转,在经济、生态与可持续性方面远远高于单纯的人工恢复投入[10]。不同的恢复措施[11]、恢复时间[12-14]对生态修复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判断人工干扰的程度和周期,控制生态恢复进程,降低在时间和资金上的投入,需要长期的数据支撑[15]。邵新庆等[16]以退化典型草原为研究对象,以空间代替时间的研究方法,探讨群落物种多样性、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等生态恢复核心指标的动态变化,了解退化典型草原自然恢复演替过程中植被演替特征及自然恢复演替的规律和能力。
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群落演替动态、结构变化影响生态系统及生产服务功能,与生产力、稳定性、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17-20]。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变化,反映了植被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包含着与演替、稳定、发展等相关的重要生态学信息[21],是最能反映生态系统恢复程度的生态学指标[22-24]。研究表明植物多样性的提高可以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对维护基本环境平衡具有重要意义[25]。选择适合的乡土植物作为退化草地的建群物种,构建不同的植被恢复模式,能够加速植被恢复进程。
本研究以阴山南麓敕勒川退化草原为研究对象,通过人工干预对退化草原进行恢复,在连续10年进行植物动态演替观测基础上,研究人工恢复和自然恢复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和演替规律,为草原生态恢复及可持续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1.1 研究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阴山南麓敕勒川草原,地处呼和浩特新城区东北部野马图村(40°55′08″ N,111°52′12″ E),总面积约2 000 hm2;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海拔1 135~1 180 m,年平均气温3.5℃~8℃,年平均降水量337~418 mm(图1);现状为山前冲积扇,多砂石,分布有废弃耕地、荒石滩、采砂石场;零星斑块状分布有羊草(Leymuschinensis)、茵陈蒿(ArtemisiacapillarisThunb)、本氏针茅(StipacapillataLinn)、白草(Pennisetumflaccidum)等[26]。研究区水样检测结果为:pH值7.66,全盐含量为296 mg·L-1。土样检测结果为:土壤有机质12 g·kg-1,水解性氮51 mg·kg-1,有效磷9.3 mg·kg-1,速效钾480 mg·kg-1,水溶性盐总量1.19 g·kg-1,土壤pH值7.97。
![图片[1]-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0-686fed308da82.webp)
图1 不同年际降水量、年平均温度变化
1.2 研究方法
按时间序列取样。2012年前研究区域为废弃耕地、荒石滩和采砂石场,场地内零星分布有原始植被,从2012年6月开始进行生态修复,保留现状原始植被,其他区域在自然地形地貌基础上用圆盘耙浅耙后进行人工播种,耱地,覆盖。播种材料有:羊草、蒙古冰草(Agropyronmongolicum)、披碱草(Elymusdahuricus)、老芒麦(Elymussibiricus)、沙打旺(Astragalusadsurgens)、草木樨(Melilotusofficinalis)、一年生黑麦草(Loliummultiflorum)。从2012—2021年连续10年监测,在生态恢复区域固定12个点(分别在敕勒川草原东、西、南、北四面分别设置300 m样线,每隔100 m设置1个点),同时在周围随机选择3个1 m×1 m样方,于每年度8月份进行测定植物种群高度(cm)、盖度(%)和密度(株·m-2);齐地刈割,烘干后称重(精确到0.01 g),获得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g·m-2)。
按不同恢复措施取样。在2018年,分别于原生草原(周边未受过扰动的自然草原)、人工恢复区域(受扰动区域在2012年播种后,至2018年实施持续管理(补播、施肥、刈割))和自然恢复区域(指不依靠人工干预或者以最小化的人工干预措施达到生态恢复的目的。本文指受扰动区域在2012年播种后,不再有任何处理)设定3个不同的处理。在每个处理设定6个1 m×1 m样方,于8月份进行测定植物种群高度(cm)、盖度(%)和密度(株·m-2);齐地刈割,烘干后称重(精确到0.01 g),获得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g·m-2)。
1.3 指标计算方法
1.3.1群落内物种重要值(Important value,IV) 是综合衡量物种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的有效指标,重要值越大,说明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越重要,通过分析群落中各物种的重要值,可以有效了解群落种群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片[2]-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2-686fed322a170.webp)
式中:
![图片[3]-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3-686fed337ef8a.webp)
![图片[4]-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4-686fed34de930.webp)
![图片[5]-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6-686fed367723d.webp)
![图片[6]-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7-686fed37f2dc8.webp)
1.3.3物种多样性分析 根据物种数目、植物种的个体数和重要值,利用以下公式计算群落多样性指标。
(1)丰富度指数
Margarlef指数(Ma):Ma=(S-1)/lnN
(2)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
H′=-∑Piln(Pi)
Simpson多样性指数(D):D=1-∑(Pi)2
(3)均匀度指数
Pielou均匀度指数(Jsw):Jsw=H′/lnS
式中:S为样地物种总数;Pi为物种i的重要值,Pi=Ni/N,Ni为第i物种的个体数,N为所在群落的物种总个体数。
1.4 数据分析与处理
用Micorosoft Excel进行数据处理,用SPSS软件对不同年际(2012—2021年)相关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对2018年度不同处理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多重比较,对物种数、个体数与地上生物量数据进行Min-Max标准化,利用Micorosoft Excel软件制图。
2 结果与分析2.1 不同年份样方物种数、个体数量与地上生物量动态
由图2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数随年际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并趋于稳定的趋势。恢复第二年(2013年),物种数由1.67种·m-2(2012年)增加至4.8种·m-2(2013年)(P<0.05)。2013—2017年物种数逐年下降,2018年物种数增加至4.97种·m-2,较2017年(2种·m-2)提高了148.50%(P<0.05),与2019年差异不显著,与2020,2021年差异显著(P<0.05)。
![图片[7]-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29-686fed395a50a.webp)
图2 不同年际样方物种数、个体数与地上生物量变化
物种个体数随年际波动,在恢复第1年(2012年)最高,而后出现下降趋势。在2013年(500.40株·m-2)和2017年(523.35株·m-2)物种个体数达到低点。植物群落个体数量在草地恢复的第7年(2018年)增加,显著高于2017年(P<0.05),与2019,2020,2021年差异不显著。
地上生物量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并趋于稳定的趋势。恢复第二年(2013年),地上生物量由26.62 g·m-2(2012年)增加至496.85 g·m-2(P<0.05);2013—2017年地上生物量逐年下降,至220.78 g·m-2(2017年);2018年与2017年相比地上生物量显著增加(P<0.05),与2019,2021年差异不显著。
2.2 不同年际物种重要值动态
物种重要值随退化草原恢复演替进程呈现不同的变化。由表1可知,2012年退化草原以零星分布的羊草和茵陈蒿为主,物种单一。在生态恢复的第2年(2013年),物种数迅速提高,以蒙古冰草、茵陈蒿、披碱草为主。2014年,植物群落由冰草属植物、披碱草属植物、羊草等构成,此时植物群落丰富,群落间界限清晰,出现较多以多年生根茎型禾草为建群种及优势种的小群落。2015年,植物群落以羊草和蒙古冰草为主,从属植物为披碱草属植物、本氏针茅和白草等,群落间边界逐渐扩散,出现数量较多、面积较大的以多年生根茎型禾草为建群种及优势种的植物群落。到2017年,整体物种数在减少,羊草、白草等根茎型禾草在不断增加,丛生禾草针茅(Stipacapillata)数量在增加,人工播种的披碱草属(Elymus)、冰草属(Agropyron)植物在逐渐减少,豆科植物沙打旺、草木樨在减少,一些新的物种如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davurica)、草木樨状黄芪(Astragalusmelilotoides)、画眉草(Eragrostispilosa)在增加。在整个恢复阶段过程中,人工引入的物种逐渐减少,土壤种子库被激活,根茎型禾草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更强,占据优势地位,到2018年度入侵物种数迅速增加。2020,2021年形成以羊草、茵陈蒿为优势种,其他多年生植物为伴生种的植物群落结构。
![图片[8]-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30-686fed3abde91.webp)
表1 2012—2021年度物种重要值
2.3 不同年际物种多样性指数动态
2.3.1不同年际Margarlef丰富度指数动态 物种丰富度指数是表明群落中物种个体多寡的参数。由图3可知,Margarlef丰富度指数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在2012年度最低,为0.137,在2013年出现峰值,随后持续减少,在2016年度达到低点,后逐渐增长。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2012年Margarlef丰富度指数与2013年存在显著差异(P<0.05);2014年与2015年差异显著(P<0.05);2015年与2016,2021年存在显著差异(P<0.05)。
![图片[9]-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32-686fed3c32b3c.webp)
图3 不同年际物种多样性变化
2.3.2不同年际Shannon-wiener指数动态 物种多样性是度量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的综合指标[27]。由图3可知,Shannon-wiener指数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2012年为0.422 9,在2013年出现峰值,至2021年持续减少。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2012年Shannon-wiener指数与2013年存在显著差异(P<0.05),2014年与2015年差异显著(P<0.05),2015—2021年差异不显著。
2.3.3不同年际Simpson指数动态 由图3可知,Simpson指数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13年出现峰值,随后持续减少。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2012年Simpson指数与2013年存在显著差异(P<0.05),2015年与2016年差异显著(P<0.05),2016—2021年差异不显著。
2.3.4不同年际Pielou均匀度指数动态 由图3可知,Pielou均匀度指数从2012—2021年呈先降低后逐渐增长的趋势。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2012年Pielou均匀度指数与2018年差异显著(P<0.05),2019年与2021年差异显著(P<0.05)。
2.4 人工恢复与自然恢复样地物种多样性比较
2.4.1不同样地Margarlef指数比较 由图4可知,自然恢复样地物种丰富度最高为1.278 5,其次为原生草原样地1.004 0,人工恢复样地最低为0.535 8。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人工恢复样地Margarlef指数与自然恢复样地存在显著差异(P<0.05)。
![图片[10]-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群落动态演替-游戏花园](https://www.hunggame.com/wp-content/uploads/2025/07/20250710164133-686fed3dbffae.webp)
图4 不同样地多样性变化
2.4.2不同样地Shannon-wiener指数比较 原生草原样地物种丰富度最高为1.066 0,其次为自然恢复样地0.927 7,人工恢复样地最低为0.429 2。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人工恢复样地Shannon-wiener指数与自然恢复样地、原生草原样地存在显著差异(P<0.05)。
2.4.3不同样地Simpson指数比较 原生草原样地物种丰富度最高为0.533 5,其次为自然恢复样地0.467 0,人工恢复样地最低为0.228 8。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人工恢复样地Simpson指数与自然恢复样地、原生草原样地存在显著差异(P<0.05)。
2.4.4不同样地Pielou指数比较 原生草原样地物种丰富度最高为0.539 3,其次为自然恢复样地0.471 0,人工恢复样地最低为0.258 2。LSD多重方差比较表明,人工恢复样地Pielou指数与自然恢复样地、原生草原样地存在显著差异(P<0.05)。
3 讨论3.1 不同年际植物群落多样性
在10年的生态恢复演替时间里,前5年为竞争演替阶段,随着种子的播入,物种在短期内大幅增加,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在2013年度出现最高值;随着物种与环境协同进化,物种数、群落密度逐渐下降,新的物种不断出现,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存留适应性更强的植物。在恢复5年后,由竞争演替到自我恢复演替阶段,新的物种逐渐出现。撂荒地恢复大致经历4个阶段:先锋植物阶段→根茎禾草阶段→根茎—丛生禾草阶段→丛生禾草阶段,其演替轨迹是从次生裸地开始,最终向该区的地带性顶极植被演替[28],本研究处于第二阶段过程根茎禾草阶段,在足够长的恢复时间里,物种会演替到顶级群落。
植物生态学理论表明,多样性提高意味着稳定性增强,即由多样性较低向多样性较高的原生植被演替[29]。随着时间推移,植物群落斑块数量增多面积增大,以羊草为主的根茎型禾草种类及数量处于优势,占据了较大的生态空间,竞争优势较弱的物种变少,另一方面新物种数量增加迅速,群落组成与结构正在逐渐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群落演替连续性和阶段稳定性相伴共存。
物种均匀度指数反映群落中物种个体数分布的均匀程度[30]。植物种类数量逐渐增加,群落结构趋于复杂化,物种丰富度显著提高,但是由于群落中建群种和优势种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能导致群落的均匀性降低[31],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2012年,研究区域植物种类较少,分布均匀,随着人工引入物种,2013年多样性指数迅速提高,物种种类及个体数量增多,使得资源利用性竞争与相互干扰性竞争激烈,种内、种间竞争加剧,均匀度指数持续下降。群落动态表明,在一个阶段内存在相应的植物群落,当原有优势物种和伴生物种优势地位下降,新的优势物种和伴生种占优势,各组分优势相当,群落又会达到一个较高的均匀度[23]。物种均匀度指数表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在达到最低值后便开始回升[11]。
3.2 不同恢复方式对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多样性比较结果显示:在退化草原生态恢复7年后(2018年),自然恢复样地与原生草原样地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明显,而与人工恢复样地差异显著,证明经自然恢复的样地恢复效果较好,群落结构组成相对更加稳定。根据邵新庆等[16]在典型草原自然恢复演替过程中植物群落动态变化结果,典型草原群落恢复的中期应该在6~7a左右,最高值出现在恢复演替中后期,即围封6a后,而后进入稳定期。宝音陶格涛[32]对冷蒿退化草原恢复研究表明,围封改良过程中多样性指数表现为具有峰值的总体下降的趋势,其峰值发生在围封后的第7年。本研究在自然恢复7年后,多样性指数接近原生草原。
人工恢复样地7年后,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与原生草原和自然恢复草原仍存在显著差异,证明持续的干扰延迟和制约了草原达到稳定状态的过程,降低了多样性。由美国生态学家康奈尔等人于1978年提出的一个假说,认为中等程度的干扰频率能维持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过度持续的人工干扰,会降低生物多样性[9]。也有研究表明:人工干预措施(施肥)能显著提高植物初级生产力改善土壤质量,打破植物地下资源权平衡以及加剧了地上光竞争,导致植物多样性下降[33]。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在生态恢复前期通过人工引入物种,短期内迅速提高物种多样性,再借助自然恢复力和种间竞争演替,最终形成以羊草为建群种的稳定群落结构。晏和飘等[34]基于2478组恢复实验,利用Meta分析对自然恢复(围栏封育)、人工辅助恢复(施肥、补播)以及人工建植(生态工程)3大类具体恢复措施进行分析,得出在中度退化高寒草地上,人工辅助恢复比自然恢复效果好。这与本研究人工干扰引导自然恢复效果较好的结果一致。
4 结论
通过对敕勒川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后连续10年的监测表明:物种数、地上生物量随年际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并趋于稳定的趋势。植物群落Margar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Pielou均匀度指数呈现先减少后增加趋势。在恢复演替10年后,形成以羊草、茵陈蒿为优势种,其他多年生植物为伴生种的植物群落结构。在生态恢复第7年(2018年),人工恢复样地多样性指数与原生草原存在显著差异,自然恢复样地多样性指数接近于原生草原。持续人工干扰会降低生物多样性,通过短期人工干扰引导自然恢复,能够使退化草原加速向原生草原演替,并维持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本研究为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实践提供依据。